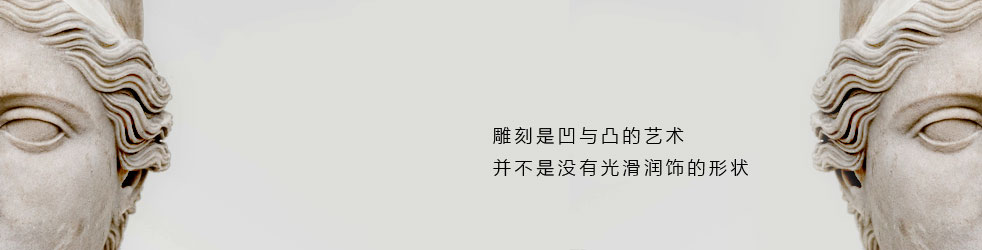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写下这个题目,不禁犹豫,唐先生曾是我的老院长,名满全国的雕塑家,还用得着我来推介?锦上添花的事情原不擅做,再,不大敢做,现今不少艺评人回避评价已得享高名者而面向将达未达者,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细想再三,还是写,原因是我写的动机,与本那些“个中原因”没有什么瓜葛,何须回避。
知道唐大禧这个名字很早,早到还未正式学画画。那时对雕塑一点认识都没有,佩服这个名字的原因,是那七十年代幅著名的国画:《人民的苹果》,所以后来知道他原来是位雕塑家,倒颇诧异。
至今还是令我不解的是,只见过他的这么一幅画作,再未见后继-那已经是很精到很成熟的国画水墨技巧,如果一直画下去,也能算一辈子吃不完的本钱了。
回忆第一次瞻仰唐先生风采,是在青年文化宫美术班的讲座上,那时的唐先生正届中年,风度翩翩美男子,讲课内容也不是雕塑,还是那张一度大热的《人民的苹果》。
深有印象的是先生的好脾气,正讲着课,来了个摄影的,摄了一通,大概觉得唐先生动作幅度太小,不似他心目中那种大艺术家的豪迈,于是上前要求摆个扬手的动作,然后拍了几张又都不满意,唐先生一急,手的幅度不觉加大一挥,卡查一下,镁光灯闪了,摄影师喊好,大家哄笑鼓掌,那一霎先生的脸便见了红晕。
后来多年未再见面。
一直到我从雕塑系毕业,在少年宫教书教了差不多一年,参加了些社会美术活动,发表了些东西,在展览会上不时遥遥一遇,也并无接触。那时的他,已经是声名赫赫,贵为广州雕塑院院长。
有一天忽然收到唐先生转来的口信,约我一谈。见了面,唐先生即开门见山,要调我进雕塑院当创作员,那时当然也挺高兴,糊里糊涂地就办好了那些个本来繁琐得要死的调动手续,进院,
进院之后,我的注意力大部分还是放在社会活动上,一直到糊里糊涂地离开。那时整个文艺界都在搞体制改革,雕塑院也不例外,而我对那些事情并没有兴致,唐院长呢,没有兴致也得有,忙得团团转,所以本该亲近时,反倒疏远了些。待我每次回国,怎么也得抽空去看看他,那已经是一种别样的感情在:亦师亦友,没有杂质,平等,平和。
我喜欢这种气氛,我喜欢他那种蕴籍儒雅,雕塑家群里,不是太粗豪就是太木讷,有书卷气的,绝少绝少。
一
唐大禧,潮汕揭阳人。
提及籍贯,因为他并不似潮汕人。比如,嗜茶、乡愿,甚至潮汕人的标识:潮汕口音,也很难在唐大禧处找到,潮汕人迷信技法、骨子里的文化保守心态在他那里更是全然欠奉,这方面来说,他算得上是一个异类。
唐大禧接受早年教育,是在香港,人们不禁会把他那一直保存着的艺术进取精神与早年这段受教育经历联想起来,其实亦不然,早年的香港,与省城的经济、文化水平相比,并无优势,亦不见得更为西化,许多留洋归国艺术家,反倒更趋保守传统。
本文不描写艺术家成材过程中奋斗的感人故事,而在其他。讨论一个人,并不见得就要得到终极答案,如果要得到答案,最直截了当的,是拿起电话拨过去问唐先生本人一个究竟。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反而,宁愿退后一些,用“陌生人”的眼光去观察,这样更有趣。比如,若有人要了解我,用采访的方式来提问,那么,我自己的回答并不是那么可靠,因为我并不完全了解自己,人更不可能完全彼此了解,那么,就让我们保留距离,距离,也许能使我们的观察更准确。
唐大禧在五十年代末回到大陆参加建设。那个时代的人,心热,纯情,且多不移志-唐大禧就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如今已经绝种。
中国的雕塑界家底非常薄,直至二三十年前基本上还是个空架子,而再早一点,连个空架子也未成型。老辈中如刘开渠留洋归国有学院经历者如凤毛麟角,多是自学成才者如潘鹤、尹积昌等。他们的人生观、知识架构与当今新一辈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其感受方向与表现方式也必然不同。个人天资与传统文化思维是他们获得成就的两大原因,因此,对西方经院式训练便难免轻视。比如出生在佛山的潘鹤,幼年所触见的石湾陶公仔,成年所接触到的罗丹流畅风格,加之唯美审美趣味与革命英雄主义的混成,天资个性,豪迈不羁,出手刁辣,风格非常明显,他接受和展开的扇区并不算广阔,却高树一帜,成为中国一流雕塑大师。
唐大禧出道略晚,如果以大类划分,是可以与那一辈雕塑家划在一起的。但细论,却又有许多不同处。
唐大禧回国后,在广州雕塑工作室任职创作,他并无高学历,在背景上也无美院的派系渊源。但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在美术学院浸淫经年也未必能有的学者气在,有时,我会想,如果他不是去了市雕塑室而是在美术学院任教,也许更适合?不知他有否由此生憾?
可谁说得清呢?美院人的成才率、成功率难道就高了?
如每一位前辈雕塑家们一样,唐大禧无可避免地带着英雄主义的情结,在那个时代,眼见到的大部是苏联、东欧,还有有限的一些希腊罗马作品,雕塑家们的营养菜单极其简单。
况且,作为国家政治宣传机器的一部分,雕塑的社会功能,也被定格在歌颂无产阶级英雄这里。
况且,英雄主义乃雕塑这门艺术与生俱来的重要基因,并无过时与否之说,当今现代主义泛滥的西方各地,英雄主义雕塑作品仍然在生产着。
其实,“说什么”在艺术范畴内只是一个很引入注目却又很不重要的因素,“怎么说”才是需要我来动笔的。
我们知道,六、七十年代乃至到八十年代,是艺术创作非常艰难的时代,无论你的创作动机是多么诚挚,一件作品上的某一细节若触到了敏感无比的政治神经,那么给艺术家带来的,很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想象力被完全压制至窒息。在这所大铁屋里,任何一点人性的微光都会我们带来狂喜,艺术的种子在巨石底下依然顽强的挣扎生长,今天看来,令人感叹不已。成功的作品如潘鹤的《艰苦岁月》,乃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艺术家们在当时的夹缝里做文章,唐大禧在这大舞台上有其高唱如《欧阳海》,然而使他突围而出的,是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猛士》。
二
一九八X年,文革结束不久,意识形态领域里,伤痕文学引发了民族情感的井喷。
唐大禧的雕塑作品引起了全国的震动。
在广东区美展中,我记忆较深的还有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另一件引入注目的雕塑则是关伟显的《彭大将军》。
《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御烈马、弯弓射日、射猛虎、射猛禽,却是一位容貌俊美、近乎全裸的少女,这少女,却又酷似当年在黑狱中被割喉枪杀的张志新。
若出自时下人手中,女子体态也难免要掺进几分雄性激素,如许多运动题材的雕塑。但唐大禧的猛士,却是完全标准比例的纤纤美女,健康,却柔美-美,就是理想;美,就是艺术的真理;美,就是艺术家的语言;美,正是这样坦荡无邪,就是这纤弱的手臂,张开了这张巨大的铁弓。奔腾的动感与优美体貌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染力。
这是中国雕塑界从未有过的能震撼人心的英雄式女性形象,以后二十年,也未曾再见过。
刚步出铁屋,在太阳底下眼睛昏花的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议论也曾引入“太出格了,不合国情的么。”这个歧路,而猛士形象的意义绝不在此,其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有关人体美的议论很快就尘埃落定,猛士却绝不过时。她定格了一个时代,她的箭犹在云间鸣响,飞向未来。
与油画《农机专家之死》相比,《猛士》不是徒为伤痕艺术的苦情戏,它沉痛,却沉痛得昂扬、倔强,她美丽绝伦。
这个形象,深入人心,亦将留存史册。
三
不知唐大禧有否作诗,至少,我从未拜读过,然而我却感觉他是个诗人,那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很罕有,尤其是雕塑家群中。
诗,文体名。一般与“文”相对。指以精粹而富节奏的语言文字来表现美感﹑抒发情绪的艺术性作品。——《国语辞典》。
诗言志,歌永言。——《书·舜典》。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选˙陆机˙文赋》。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歌是最高的艺术体裁。……诗歌用流畅的人类语言来表达,这语言既是音响,又是图画,又是明确的、清楚说出的概念。因此,诗歌包含着其他艺术的一切因素,仿佛把其他艺术分别拥有的各种手段都毕备于一身了。诗歌是艺术的整体,是艺术的全部机构,它网络艺术的一切方向,把艺术的一切差别清楚而且明确地包含在自身之内。——别林斯基《诗歌的分类和分科》。
雕塑是一种凝练的艺术样式,却不等于所有的雕塑都具备诗性,因为,诗性不仅仅是凝练。
唐大禧的雕塑充满了诗性,与其体现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相比,现实主义的因素在他的作品里只占一个次要的位置,我甚至怀疑,如果不是当时“革命现实主义”的框架太大太沉重,他有可能走得更远。
其后为汕头图书馆创作的《启明》,为常州市中心广场创作的《未来属于我》两件作品,也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创作立场。我这里使用“立场”这个词,是有意的。因为,由世界观价值观衍生而来的创作立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尽管如今许多人竭力避免谈及,却其实无可避免,尤其谈及前辈艺术家的创作,根本就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健康、饱满的生命力,抒情、信心十足的精神面貌,对未来的憧憬,对国运上升的召唤,基本上是唐大禧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创作基调。也是他声名鹊起的原因,因为,他走在时代意识形态前面。
我想,大概是因为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无能传达他心中奔腾的诗性,所以在《人民的苹果》之后便搁下,他找到了更好的媒介。
那是他创作的盛期。
纵然是抒情小品,也是灵性十足,比如一件几十公分的石雕《十五的月亮》,就深深感动过我,那就是诗,小诗,诗的好坏诚不在规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与刘开渠、尹积昌等老雕塑家相比,他是幸运的,时代终于给了他展现才华的舞台。
相反,唐大禧的创作手法并不似其他雕塑家那样固定。在技术上,他的手法并不似潘鹤那样绘画性浓重,手法那样酣畅狠辣;也与梁明诚的华丽流畅有明显区别。他的作品,体积上的高点与低点对比不大,比较柔和,多细部变化转折,但这些说来价值不大,每个艺术家自有其习惯,或者说,风格。
风格手法的固定与否,并非我们常用的二元论思维的“好”、“坏”便道得清,进步与保守的标签,使用起来非常便当,而这种不经大脑的思维方式,正是目前文艺批评的泥沼。
四
温文尔雅的外表内,唐大禧绝对是个倔强的人。
艺术家不能不倔强。
好胜之心不息。
艺术家岂能不好胜?
城市雕塑兴起,雕塑家们被时代从展厅赶出了室外,许多人头昏目眩。
大部分的雕塑家手下的作品,仅仅是展览品移到了阳光下,其公共艺术的语言并不谙熟,很遗憾,二十年一挥,至今,尚未发现有长足的进步。
城市雕塑-空间艺术,它的语言当然地不能与室内展品一样,它的构成要复杂得多,吃经验主义的老本,必定落伍于时代,唐大禧深知这点。
令人惊异的是,他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每一件之间都使用着不同的手法。如果说个人风格的“不固定”,我认为他是最典型的,这就是才气带来的自信。
贫鄙之人,捡得一铢便深谨收藏;豪客一挥,千金散尽还复来。
他永不落伍,永远在变,如果一个人不大度,不开放,这是无法想象的。
这样写,毕竟还是说好话了,还是带有二元论的意味。
《创造太阳》,一九八八年作。
同样是昂扬激奋的主题,看题目可知。
但主体对象的个性基本消失,以形式感取代之。
青铜塑造手法与闪亮的不锈钢造型结合,大面块,大开大合。
然而这件赢得全国美展铜奖的雕塑,我个人认为,只是唐大禧的一个转型期的记录而已。用造型诠释意念的手法上,它含糊生硬,特别是不锈钢部分的造型,纯以三度空间的技术要求论,更不成熟,放置在室外空间里问题更大。
同样,在广州雕塑公园门前的华夏柱群,也未见成功,缺乏震撼力,不客气地批评一句就是:堆砌古董。
与装饰意识有关。
在前文我已经提及创作立场-立意对作品的巨大影响,这里同样适用。
对人生的感悟深度,对主题内涵的发掘能力,是前辈艺术家最明显的优势,若离开这点,过多地把精力投向形式感,那么,作品只能暂存而已。
而筋脉过多,诠释性越强,艺术的醇度便相应降低,如宋人作诗之毛病。
表达与表现,是两个层次。
如潘鹤先生那把折断了的巨型鸦片烟枪,就基本脱离了艺术语言。
而只要艺术家的创造力仍在,那么,佳作与否,都成过往。
今年,在唐先生的工作室里,我看到了抗击非典女勇士叶欣的胸像,柔美,洁白,浑成一气,又是一个女勇士,然而,她不是怒目问天擎弓策马,只是安详、泰然,勘破了红尘生死,如菩萨舍生,这勇,又是出人意料。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不觉有难言的欣喜在。
我永远,相信唐先生的创造力。
谨以一篇七绝赠与唐先生并作为此文作结:
启明起处立苍茫,人境飞尘化鬓霜。
信有雕龙心未了,云山石屋起铿锵。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后记:
此文写就,不觉忐忑,思量再三,还是发上来了,事先并未经过唐先生首肯,有惶恐在。然,美术界学风,素来非谀则诽,或隔靴搔痒,或宝塔梦呓奥而无妙以非汉语文法标榜者多;而雕塑界,欲求前述恶文尚且稀少,几无学术声音,失血之躯,能长命乎?历史原因下,此废待兴,开学术言路风气,正须从吾辈始。
未敢以本篇言学术,谨以一观众立场作言而已。唐先生才志高卓,襟怀正大,素来对晚辈冀望甚殷,必不以文中谬误、臆想及不恭之语厚责于我。
2005年2月立人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发表评论
请登录